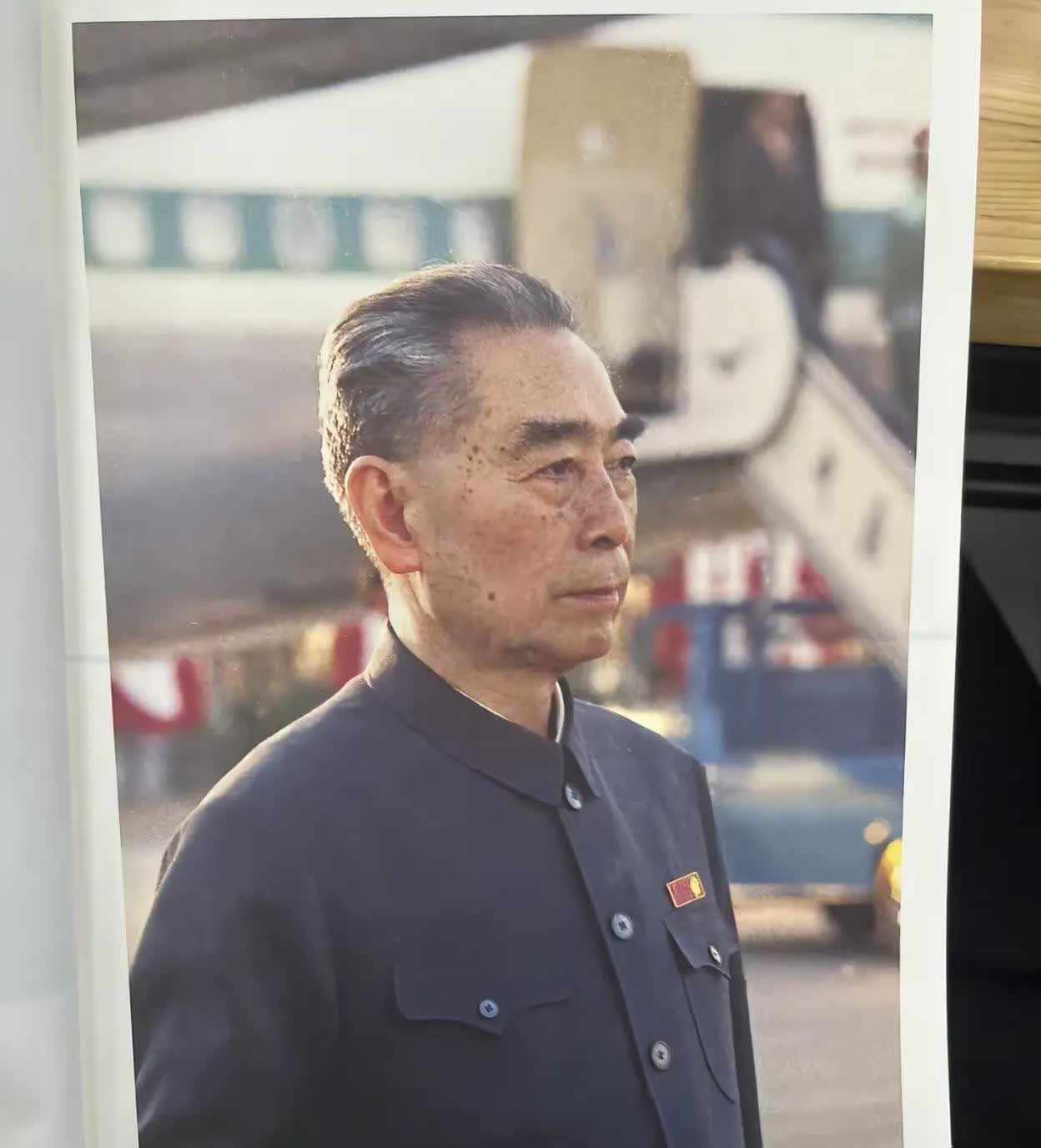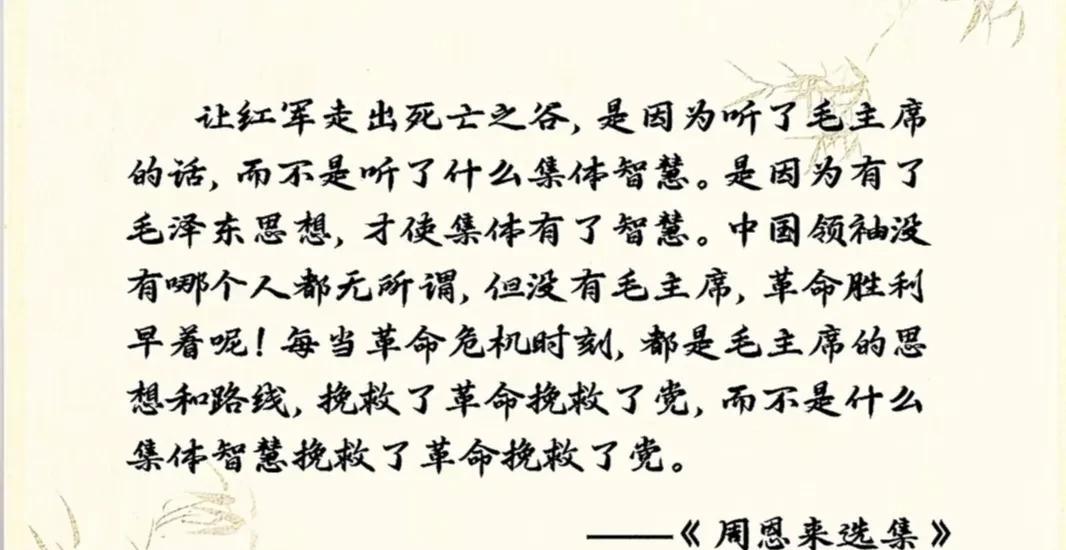南昌起义的时候,没有贺龙,可能都搞不起来。因为当时说是要参加起义的蔡廷锴临时不参
南昌起义的时候,没有贺龙,可能都搞不起来。因为当时说是要参加起义的蔡廷锴临时不参加了,导致起义军的实力大大削弱。而剩下的起义力量就是贺龙的嫡系部队以及叶挺的部队了。贺龙这个人啊,在南昌起义那档子事里,真的不是可有可无的角色。说一句“没有他,南昌起义都干不起来”,并不夸张,反倒是历史事实在那儿摆着。当时是1927年夏天,国共之间的关系已经彻底撕裂。武汉那边的汪精卫,南京那边的蒋介石,一个比一个反共。还要硬顶着这种风口浪尖,发动一场军事起义,地点选在南昌。这个时候就得看谁肯站出来了。说是三家部队要干:贺龙的第二十军、叶挺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,还有蔡廷锴的第二十五师。结果临到头,蔡廷锴掉链子了,临阵退缩。他不干了,这一退,起义部队的实力就一下子瘪下去了,兵力差不多直接少了三分之一。叶挺的那支部队,虽然政治坚定,但说实话人数不多,火力也一般。真正扛得起场子的,还得是贺龙。但问题在于,贺龙那时候还不是共产党人。这种时候,他要真一犹豫,南昌这事儿很可能黄了。可贺龙偏偏就没犹豫。早在几个月前,北伐途中局势就有变化,不少将领纷纷“清共”,有的干脆投奔蒋介石,把原来身边的共产党人全赶走,甚至逮捕。贺龙却是少数几个反着来的。他对自己部队里的共产党员说:“不要怕,不要走,继续干。”这在当时,是顶风作案。武汉“七一五”事变后,汪精卫反共彻底撕破脸,大抓共产党人,街头巷尾一片风声鹤唳。贺龙这边,却像是另一个世界。他调兵把工会农会的门口都插上第二十军的军旗,还安排士兵站岗放哨。这摆明了是给共产党人撑腰。这样一来,第二十军成了“红色避风港”。这些安排,不是哪个命令下达的,是他自己决定干的。当时蒋介石、汪精卫的人还派人来“套近乎”,意思也很明显,愿意给他高官厚禄,只要他跟共产党划清界限。贺龙一笑,说:“从民国三年我就听你们讲革命,现在翻脸杀人,比唱川戏还快,我才不跟你们玩。”共产党人不是不担心他变心,周恩来赶到九江,跟他当面谈话。贺龙倒没拐弯抹角,直接说:“我服从共产党的安排,一切听指挥。”说得干脆利落。这句话,等于把他的政治立场摊在桌面上。中共中央那时候已经决定由周恩来负责南昌起义,组建前敌委员会,其他成员还有李立三、恽代英、彭湃等人。他们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任命贺龙为起义军总指挥。贺龙一听,愣了下,说:“我还没入党呢。”周恩来开玩笑似的说:“怎么?你不是说一切听党的嘛?这第一条命令你就不听?”贺龙笑了,说:“那就听。”说听,其实是背水一战。他清楚地知道这意味着什么——要和蒋介石、汪精卫彻底撕破脸,要和张发奎脱钩,要把自己的军队推向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队伍。这是一步大棋,没人逼他走,是他自己选的路。南昌那边,敌人也不是吃素的。朱培德的警卫团早就接到了风声,严阵以待。关键前夜,还有个副营长叛变,把起义时间、兵力部署全泄露出去了。情势急转直下,前敌委员会只能紧急决定,原本定在凌晨四点的起义,提前两个小时打响。贺龙亲自坐镇指挥部,和刘伯承一起布置作战。他们的位置,就在敌人枪口不远处。外头枪声大作,子弹在头顶飞,他们站在石阶上不动,观察敌情、调兵遣将,指令一条条下达。那天夜里,南昌的街道被点亮的不是灯,是马灯和火光,兵士身上绑着红布,左臂系白巾,口令是“山河统一”。第二十军的第一师,硬生生啃下了旧藩台。鼓楼被封锁,敌人死守阵地不退。贺锦斋、刘达五两位老将,一个带人翻墙包抄,一个正面强攻,用火力压制再逐屋清剿。不到两个小时,敌人被赶进大院,集体缴械。教导团、第二师、叶挺的部队同时发起攻击,小营盘那边的守军甚至主动交枪,大营盘扛了几下也撑不住。整个战斗持续不到四小时,敌军三千人要么被俘,要么投降。起义军的旗帜在总指挥部楼顶飘起来的时候,是清晨六点,天还没亮透,整座城已经易主。这一仗之所以能打下来,靠的就是贺龙的调度和他手下的兵。很多人后来都说,南昌起义是共产党打响的第一枪,是武装斗争的开端。话没错,但枪是谁打的?是谁把枪口对准敌人?是谁撑起了第一线?细究下来,答案其实很清楚。贺龙不是“被动卷入”的人,也不是“受命参与”的将领。他是主动选择站队、主动挑头干事、主动承担风险的人。他和叶挺、周恩来等人密切配合,不只是“参与”,而是“主导”了整个起义流程。从军力分布,到作战计划,再到指挥节奏,都是他亲自盯。事后总结,南昌起义胜在三点:时机果断,计划清晰,兵力集中。而这三点里,贺龙至少扛了两点。如果他当初动摇半分,哪怕犹豫一天,局势就可能反转。蔡廷锴已经退了,叶挺一人独撑太难,如果贺龙也退,那这仗真打不起来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说“没有贺龙,南昌起义可能就干不起来”,并不是拔高,而是还原。他是起义的主心骨,是稳军心的那块砖,是从政治表态到军事落地都站在最前头的将军。